過去數十年來,關於侯導的電影研究與論述已有非常多的故事細節、書籍文章及相關當事人的回憶與說法可以提供佐證,然而現在印刻又出版了最新、也是最完整的一本:《煮海時光:侯孝賢的光影記憶》,係美國電影學者白睿文(Michael Berry)與侯導的面對面深度訪談,從侯導的童年往事到他進入電影圈一路走來四十年,從《就是溜溜的她》到還未面世的《聶隱娘》,每一部片的拍攝過程及細節都儘可能地追索提問;同時亦訪問了演員高捷、作家朱天文與黃春明,由側面對侯導的說法提供印證或旁證,最後再由朱天文進行校訂,這本身就是一件記憶處理的工程,幾乎也可說是台灣電影史非常重要的一塊,對於一個即使在世界影史都不容忽視的台灣導演,此書實在是不可或缺的一本!
這樣的回憶工程,不僅僅是對歷史交代而已,對於我們理解電影導演的創作理念及方法,甚至理解電影本身,都有著相當的重要性。
從現有的電影文本而言,其實比較侯孝賢、楊德昌這兩位同時崛起的台灣新電影大導,可以明顯看出兩人的創作方法之不同。
侯導從《風櫃來的人》已經可以看出反傳統(古典)敘事的企圖,而楊導《海灘的一天》變換時序的剪輯在手法上雖然非常前衛現代,但整部片仍然比較重視亞里斯多德《詩學》中所謂「故事必須具有完整性」的概念,縱使形式上已經打破了開場、中段與結尾的古典敘事結構,但情節上的因果關係仍舊係理解楊導電影的重點。
從攝影機角度看,侯導的《悲情城市》、《好男好女》多以旁觀者角度維持對影片中事件人物的距離,僅呈現某種自然或真實;同樣採取旁觀者角度,楊導的《恐怖份子》、《牯嶺街》卻明顯表現出其在文本之上的超然位置及其批判性觀點。
在對現實的反映這點上,侯導的《童年往事》、《冬冬的假期》可謂亂中有序呈現自然;楊導的《青梅竹馬》、《一一》則體現了去蕪存菁才能現出本真(註1)。
落實到演員表演時,楊導要求精準,所有對白都字斟句酌以力求能表現觀點,所以演員必須以演技配合,從走位、鏡頭運動到場面調度全都得聽導演安排,例如《獨立時代》、《麻將》;楊導講求犀利結構,有如「庖丁解牛」,要完美呈現這點,演員必須要能達到導演的要求。
而侯導由於重視角色真實而自然的反應,多以設定情境、設計情節讓演員自由發揮,例如《戀戀風塵》、《南國再見,南國》;這種拍攝方式的偏好逐漸形成侯導的長鏡頭美學,演員多半被要求自然演出自我的真實反應,即使是《紅氣球》裡的茱莉葉‧畢諾許(Juliette Binoche)(《煮海時光》,頁269);許多時候侯導都「放牛吃草」,演員甚至不清楚攝影機何時在拍,《咖啡時光》的余貴美子便曾苦惱侯導不喊卡(《煮海時光》,頁242)。
也因此,以「電影感」(註2)而言,侯導的片子在完成前每一格都可能是多餘、未完成,只要電影感對了才被放進來,感覺不對就刪掉也無所謂;楊導則經過精密算計謀畫布局,每一格畫面都有意義,不可去除。
歸根結底回到兩位導演對歷史的看法,雖然歷史真實千絲萬縷,電影只能擷取部份,但差別是兩人擷取方式不同,所以侯導在拍片現場之前都會設想好許多片段情節,這段拍不出來或拍得不好沒關係,反正還有其他片段,只要人物角色性格是一致的,到時候選出最好的剪進來就好,情節不重要,頭尾不重要,甚至畫面不連戲都無所謂;楊導則無法這樣拍片,開拍之前經過長期反覆思考精心設想,所有的畫面其實都在他腦子裡,要是有一段關鍵戲拍不出來或始終拍不好,解決方式之一可能就得換演員了,此所以吳念真曾苦笑著回憶說《一一》裡光是一場從喜宴會場回家的開車戲就拍了好幾次,因為換了好幾個女兒。
以上這些差異性的比較中關於侯導的部份,都可以在《煮海時光》書中得到印證及進一步理解的線索。
又例如書中白睿文問道:「像《風櫃來的人》有多少對白是根據劇本,又有多少是您讓演員即興發揮?」侯導回答:「通常是有個劇本有對白,但是這個對白只是給他們知道有這對白,可以增加或是減少他們都已經習慣、很清楚了,尤其是高捷。這些都很容易,因為我現場是不帶劇本的,就一直盯著演員,不合的──就是不合氛圍的──就不行。到《千禧曼波》更是,哪裡有對白,只有一個氛圍形容這場戲……。」(頁116)
侯導在拍片現場大多都沒腳本,那麼有固定腳本的《海上花》他怎麼拍?侯導說:「……有時候拍不到,我不會勉強的,就跳過,改天再來拍。不要一直拍,演員沒有就是沒有,要隔了以後再拍。要是真的拍不到,就重新設計──情感是一樣的,換一個表達方式。我通常就是這樣子。但這一次拍《海上花》沒得改,因為對白就是那樣。所以一輪一輪,鏡頭的移動就跟著調整。」(頁217)
由於總是有人將侯孝賢的電影與小津安二郎相提並論,認為侯導某些鏡頭的運用若非受到小津影響便是向小津致敬,這些表淺的看法甚至已經形成某種迷思,所以侯導才會藉由在1998年於東京舉辦的小津電影研討會上發言的機會,說明自己與小津的不同。
日本影評家蓮實重彥亦曾在〈當下的鄉愁〉文中說道:「侯孝賢認為自己與小津無法進行類比,其原因明確地說就是小津電影的特性在於過去的缺席。」(見國家電影資料館出版之《侯孝賢》專書,頁71)
然而侯導當時僅說道,小津幾乎都是拍現代,而他自己幾乎都是拍過去(彼時除了半部《好男好女》及《南國再見,南國》是拍現代外,侯導其他電影都是拍過去,另一部也是拍現代的《千禧曼波》則尚未開拍);這只是針對拍攝內容而言,若是從電影創作方法來看──正可以《煮海時光》為證──侯導與逐格底片都要精算的小津可說有著根本上的不同。
從書中訪談亦可發現每當白睿文試著舉出某部電影中的某個畫面,或著某個鏡頭運用,又或者某個場面調度,是否具有如此這般的象徵意涵之時,侯導若不是直接打斷,或斷然否認,就是表明只是偶然、沒想那麼多,甚至在被問及《風櫃來的人》和《戀戀風塵》關於父親身殘的象徵性時,侯導乾脆直接回答:「我通常不管象徵性,只管順不順,對不對,象徵意義是別人去發現的。……這都是記憶和經驗。你要我這樣拆解沒辦法,我要是這樣拆解就不會拍了。」(頁115)
當然電影的創作方式並不是評價電影的絕對標準,這只是幫助我們釐清導演的美學形成的源頭,並且讓我們看到侯導的美學可以被發掘、詮釋到何種地步。從侯導說《風櫃來的人》劇情稀薄到觀眾都追不到故事線索(頁122),到《戲夢人生》幾乎可以說完全不要故事了,只有片段式的情節,以半演出、半紀錄的方式穿插主角李天祿的旁白自述,李天祿本人的一生已然是個傳奇,但侯導以此片再現李天祿的人生則成就了另一個電影史的傳奇。
朱天文在《劇照會說話》一書中提到黑澤明看侯導《戲夢人生》,記者問這部好像不太像(一般)電影?黑澤明怒斥:「不是!它就是完成的電影……我自己拍電影有時會覺得不像電影!」(頁119)
雖然認識一位電影導演最好的方式還是透過他的電影,但是對創作過程的訪談往往能提供必要的補充,讓我們在影像及語言文字的來回印證之中得到更多更深入的理解。甚至我得說:《煮海時光》不只是目前為止認識侯導電影的最佳書籍,更是認識台灣電影一路走來四十年的重要史料,而我很遺憾楊導沒機會也來上這樣全面又完整的一本。
※本文刊於2014年《本本/A Book》雙月刊第5期
註1:簡單說,侯導的電影其故事、因果都不重要,他所見的真實人生(或歷史)從來不是直線的因果所形成,而是紛亂無由的,但其中又似有某種大自然的秩序在運行(他的想法其實比較偏向傳統中國哲學);楊導比較西化,他認為敘事的本質就是應該從雜亂無章的表面抽絲剝繭呈現出人生的實相,與此無關的都應該去除,至少不必表現出來。
註2:何謂「電影感」?這三個字如果問十個人可能會有十一種答案,我只能說這是導演在處理自己電影時的某種sense,侯導曾使用「氛圍」二字說他如何處理拍攝現場無劇本的情況,「氛圍」二字拿到剪接台上就是「電影感」,對不對只有侯導自己知道。楊導的「電影感」則絕對不是「氛圍」二字,而是演員對白、攝影角度、場面調度等等一切安排都達到他的設計要求,那時他才會說「對了,這就是我要的電影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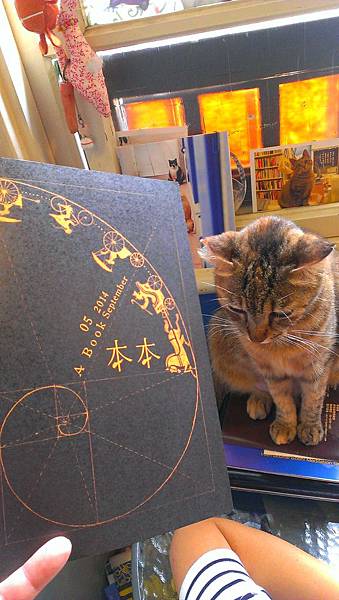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